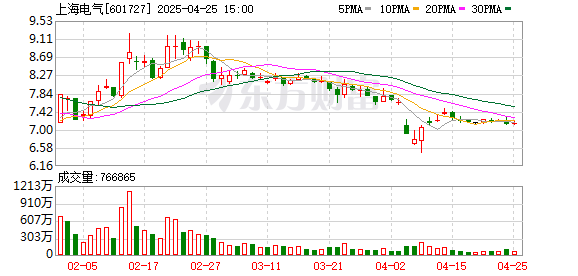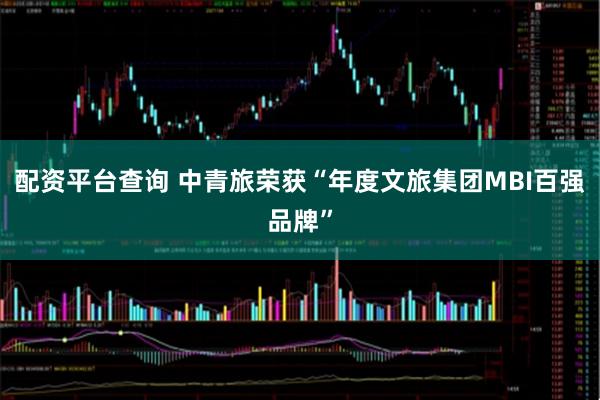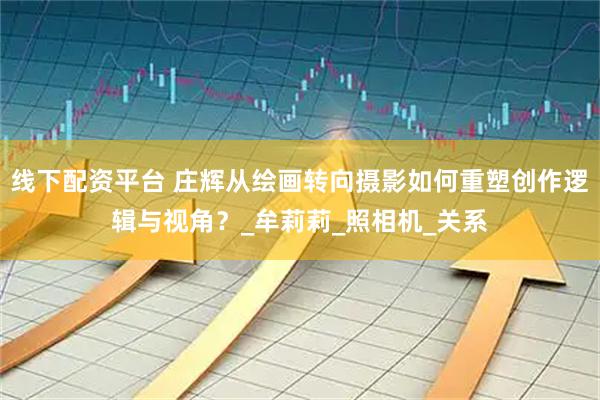
在你几十年跨度的创作生涯中线下配资平台,虽然历经不同的社会文化发展阶段,但你是否会觉得器材技术的发展对于创作的影响在目前的艺术史书写中被忽视或是被低估了?
确实,我感到在国内外技术条件越来越接近的当下,国际间的创作好像越来越同步,甚至有些重叠。技术的突然进步,其实帮我们追赶上了一些曾经缺失的文化视角。例如无人机影像创作,中国作为无人机生产大国,相应的作品好像与其他国家相比也更丰富、前沿。 有时候思考摄影文化和技术生产本身的关系还挺有趣。
20世纪80年代你还在做工人时自学了绘画,那时的画作也基本上是风景写生之类的作品,还没有介入太多对观念性的思考吧?
地平线下有一片土地当作参考物,然后再加上一些植物,或是什么天空之类的内容,基本上是这样一种视觉模式,有点像风光摄影的感觉。画面会根据颜色关系,比如阳光和老旧的厂房形成的阴面和背面之间的关系,我往往会被这些色彩打动。或者有时甚至没有具体的景物,而是一片很大的旷野,它能把一种情绪调动起来。
展开剩余91%庄辉与牟丽丽合影 ,1990 年
练东亚与牟丽丽合影,1990 年
寻找牟莉莉,2011 年 庄辉
1990 年夏天,我和一位朋友从洛阳骑自行车到拉萨,途中经过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在招待所认识了一位当地的姑娘牟莉莉,她很好奇我们的行动,并带我们去附近的当金山观看落日。我们两个人分别与她合了影,这两张照片我一直保存着。 2011 年我又路经此地,看到的和我20 年前的记忆完全没有关系。询问当地人后得知,我到达的是一个多年前已经搬迁的新城,老县城已经被废弃,在地图上只能找到博罗转井镇的名字。一路上坡,车开了约半小时,我们来到“故城”,到处废墟。后来我将当年的这两幅照片,分别画在博罗转井镇的两堵土墙上,标题是《寻找牟莉莉》。
但似乎从1992年开始,不管用摄影记录行为艺术创作,还是完全将快照作为作品的“十年”系列,你去再现事物的视角,或者说是需求就完全变了。这些日常生活里较为随意的画面,和传统绘画的形式、题材相比都有很大的不同,这是不是摄影这一媒介本身带来的创作逻辑的变化?
也许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我接触比较多的是行为艺术。当时我看行为艺术的现场表演时会感到,表演是一种东西,但事后看记录表演的照片时发现,照片里的现实又是另外一种东西,而且它的表现能力比现场所感受到的更强烈。
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在思考,既然照片与现实是这样的关系,为什么我不考虑用摄影本身去做作品呢?也就是沿着这样的思路,我开始慢慢地用照相机尝试做一两个人一组的合影作品,后来发展出“大合影”系列。后来的“公共浴室”系列也是因为当时我拥有了一台奥林巴斯相机,有自动连拍和自动曝光功能,并配合着高速胶卷才得以完成。
通过相机的镜头看出去的世界,实际和用画画时肉眼的视野不太一样。写生的时候,看着前面这“块”景物,其实感官的整体感受更强烈。当然摄影也是你感受到刺激后,才把相机拿出来,但当你要面对一个具体的物体,并进行对焦时,取景框决定了你的位移和选择。二者有比较微妙的区别。
那个时候我有一点痴迷摄影,经常会出去旅行,走到哪拍到哪。其实这种创作逻辑就和绘画很不一样了。因为它可以随手拿出来拍,考虑的东西很少,更多是一种直觉。技术的进步让人的感官更加“视觉化”,变得更敏感,或者是警觉性更高,我甚至认为它会改变我们的基因。比如说我拍了很多干农活的人,按快门的瞬间很多改革开放前的场景和画面就一下在我的脑海中被调度出来,比如哪个地方有一个人使得构图更合适,这些经验源源不断出现。很多人说这些照片传达了一种中国人看自己的世界的眼光。不是方式,就是眼光。
公元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日洛阳市一拖公司七号幼儿园全体师生合影纪念,1997 年 庄辉
公元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三日河南省安阳市道路绿化管理站全体职工合影纪念 ,1997 年 庄辉
“大合影”系列的创作动机是什么?回头看这个作品处于一种工具性的影像应用和当代艺术的观念之间,而且嵌合在非常具体的历史语境中。
我考虑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多义性。多义之一是指摄影术与其自身的传统之间的关系,因为创作这个系列时,也就是1996-1997年,国内电脑开始普及,大家已经意识到视觉的世界要被打开。我也在思考摄影究竟是什么,相机的基本功能是什么。因为一个事物不管最后发展的程度如何,我认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当初发明它的原始功能。摄影术的历史不是很长,而这种长卷合影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就更短,这些问题关乎技术和传统之间的关系。
另外就是我对中国当时现状的思考,过往的大集体式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在瓦解,而相机的普及恰好代表了一种个人独立意识的普及。我那时还算年轻,有点敏感,觉得在这样的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摄影正好可以用它独有的方式见证这个变化。
东经 109.88 北纬 31.09,1995 年 庄辉
1995 年 4 月,我去了长江三峡。那里刚刚开始修筑三峡大坝,我在三峡大坝坝区主要的自然环境中选择了三处地点进行打孔。 第一段选择在大坝的原址三斗坪,当时这里是一个工地,我用探铲打了一处三角形的排孔。 第二段选择在巫峡的江岸上,每隔 20 米打一个探孔,共 51 个探孔。第三段围绕白帝城四周打孔。
你谈到了社会本身的历史变化,也谈到摄影的历史。你觉得在你身边,这两者的交叉点还有哪些?
我觉得20世纪后30年那段时间里,大家对于摄影的理解基本上还是按照那套由上至下的宣传美学理解。我年轻的时候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视觉作品的制造与传播权主要集中在摄影记者手上。但我认为他们中很多人会产生一种错觉,即把自己的工作要求当成一个行业、文化的标准。当然,那个时期海外来中国拍摄照片的西方摄影师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一样,如所谓的马格南摄影师等,只是大家彼此使用的视觉语言不同,感觉他们都在用一种很挑剔的眼光看这个世界。而我则希望能把对象拍的如其所是,每一个对象都是一个时代中的独立的存在。
你个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创作和那个年代大众所接受的主流视觉经验的关系?
对我个人而言,它肯定是一种分离的关系,因为我主动要从那个文化范式中挣脱出来,是对抗性的。但是到了今天,客观地将二者放在一起看,就更像是历史中两个并行的线索,可以更完整地看到当时人们不管是对技术或者对艺术的理解,乃至对社会的理解。
晚霞,“十年”系列,1992 ―2002 年 庄辉
羊羊,“十年”系列,1992 ―2002 年 庄辉
小三峡上游的水泥厂 ,“十年”系列,1992 ―2002 年 庄辉
摘花,“十年”系列,1992 ―2002 年 庄辉
甘蔗林,“十年”系列,1992 ―2002 年 庄辉
水库大坝,“十年”系列,1992 ―2002 年 庄辉
在山顶,“十年”系列,1992 ―2002 年 庄辉
当代摄影创作在中国虽然发展时间不长,但在近年也发展出很多套不同的视觉范式,并不断被许多艺术家复制、模仿,那似乎也是一套创作的程序,也是一种限制?
因为它也变成了一个个制度性的东西。当一个作品要进入画廊、美术馆、博览会,这样一个完整的系统无形当中就形成了另外一种创作的组织模式,形成另外一个圈子,一种替代性的组织结构,大家的目光也越来越世俗。我常常认为艺术家也分两种,一些痴迷于艺术史里边发生过的历史,他会注重自己的作品与历史的关系和逻辑;但还有一部分人是在现实巨大的压力之下,试图对自己的诉求进行表达。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在我们社会近几十年发展中,如果大家都开始做风景了,或者看到大家开始大量讨论风景,其实往往是发生某些重要事件或是重要现象的前奏。
我的意思是,更细致地说,西方的当代摄影创作虽然受身份政治等诉求的影响很大,但总体还是呈现比较丰富的创作方法论与样貌,有各种不一样的风格流派。但当它们被引入中国后,有关“景观”的风格似乎很强势地成为主流。在你的创作脉络中,虽然没有直接有关风景或者是有关山水的主题,但大多数都以户外,或是自然环境为背景,比如三峡、祁连山等,有人和你提及过这个问题吗?
我想,可能中国因为有道教的传统,有“道法自然”这样延续几千年的说法,所以它很容易在欧洲等地的“风景叙事”介入国内的时候产生一种共鸣。所以一大批国内艺术家开始跟风、模仿、抄袭我觉得都不奇怪。另外,风景也是历代中国艺术家在具体历史环境中的选择。我觉得潜意识的影响也有,主动选择的理由也有。对我来说每一个创作都是必须真的和自己相关,比如童年记忆等。另一方面我很少拍人,也没有画过人物,我觉得人是世界上最不靠谱的东西,善变,没有牢固的感觉。所以我就主动将创作偏移到我能把握的东西上,比如面对一个风景。人和人之间交流的复杂情绪很多,我害怕这些。
安西风口(红外远程彩信相机,数码打印),2014 年 庄辉
安西风口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由于特殊的大气环流和地形,使该地区年平均风速达 3.7 米 / 秒,最大风力达12 级。它与北欧风库、北美风库并称为世界三大风库。 我将一部具有远程适时传输彩信和 E-mail 功能的相机放置于安西风口某一区域,通过预设定时,相机会每隔两小时拍摄一张图片,并将图片以 E-mail 方式适时传输到作者的邮箱。拍摄时间 :2014 年 7 月 1 日 13 点 47 分起,由于夏季受极端高温气候影响,相机于 2014 年 7 月 15 日 4 点 48 分停止工作,其间共拍摄传输了 123 张图片。
大量当代影像完全不是以人的视角为出发点,甚至没有地平线,它们来自监控或是从天空垂直向下的卫星。那是否如你所说,这些视角下的影像更没有“安全感”,这种风景你也没什么兴趣?
我确实没兴趣,实际我在做“祁连山系”的时候,无人机已经在市场上铺开,好几个朋友建议说“从无人机的视角再看这些大山大川是不一样的”,但我好像不需要那样的角度。“壮观”是很好看,但我并不需要,那种视角离自己的内心比较遥远,那是一种权力美学。“普世”“宏观”地看一个事情,必然会忽略个人生命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因为我是从宏大叙事中解放出来的一个人,所以未来我不愿再回到那样的一个意识中去。我有我自己的视角。
无人区”艺术项目,2014 年 庄辉
无人区”艺术项目,2014 年 庄辉
现在的文化环境和技术环境和1990-2000年代相比大为不同,你怎么看当下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创作。
1990年代是向往全球化的时代。大家在相互观望线下配资平台,外界对中国也有一种陌生感,相互打量。但现在不一样,大家都看清楚了彼此,相互瞧不上。所以这又迫使你回到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地理”当中来。我是谁,我究竟在干什么。当然,这时候一些人就会保守、自大。但更应该做的事是回到自己的空间里,细心地耕作自己的土地。
发布于:四川省爱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